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環境事件發生后,國家和江蘇省各相關部門迅速跟進,展開全面調查。這一事件,讓很多人對場地污染問題倍加關注。
場地污染形勢如何?
據估算我國污染場地達30萬—50萬塊,今年將開展詳查
十幾年前,袁女士在所居住大城市的中心地段購得現有住房,如今,這里交通便利、公共設施齊備,房價飛漲。但袁女士住得并不是十分安心——這里曾經是一處密集的工業區,小區所在地塊原本是一家木材廠。“木材防腐、油漆噴涂,都需要很多有毒的化工產品,土壤里不可能沒有殘留。我買房那會兒,還沒有土地修復這個概念,也就是說,我們腳底下的土地或許還存在污染。”
袁女士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土壤污染主要包括農業、礦山、場地污染三類,袁女士關注的屬于場地污染。2014年,國土資源部與環境保護部共同發布的第二次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在調查的81塊工業廢棄地的775個土壤點位中,超標點位占34.9%;在調查的690家重污染企業用地及周邊的5846個土壤點位中,超標點位占36.3%;在調查的146家工業園區的2523個土壤點位中,超標點位占29.4%。
就是這樣一個被業內專家普遍認為尺度大、精度不夠的調查,依然暴露出這么多的污染問題,場地污染形勢可見一斑。中國環境修復產業聯盟秘書長高勝達認為,目前,我國有污染場地30萬—50萬塊。
“這是根據美國污染場地數量和中美兩國制造業情況對比估算的數字。”高勝達說,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雖然得出了土壤環境質量的宏觀情況,但并沒有“摸清家底”——點位超標率不能指導實際的治理修復工作。年初的全國環保工作會議上,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透露,今年將開展土壤污染詳查。業內人士期待通過此次詳查,摸清耕地和建設用地污染情況,其中排查污染場地是一個重要方面。
不像空氣、水所遭受的污染那樣看得見、聞得著,場地污染通常表現得很隱蔽。在zui近舉辦的“中國土壤修復現狀與問題”沙龍上,專家表示,就場地污染而言,土壤污染并不一定會產生實質性的危害,危害的產生以及大小主要是看在一定時間段內,有多少污染物通過不同途徑(呼吸道、口、皮膚等)為人體所吸收。
對此,從事污染土地評估工作的浙江大學空氣污染與健康研究中心副教授堯一駿表示,當土壤污染程度相對較輕時,其危害往往被人忽視。但實際上,人體長期暴露在低濃度污染物下,也會對健康產生損害,因此應重視土壤污染問題及針對污染物暴露途徑的防護措施。他特別提醒,這幾年,很多學校開始選址修建新校區,選址過程中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造成的健康風險一定要重視。
污染地塊是否都需修復?
“治土”不能依靠巨大資金投入,科學的方法是“分類管理”
土壤污染治理是與水、氣治理并列的環保“三大戰役”,與“大氣十條”“水十條”類似的治理綱領性文件“土十條”呼之欲出。業內一度傳言“十三五”期間相關投資將高達兩萬億元的規模,土壤修復企業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
高勝達坦言,受“土十條”、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政策法規預期影響,近幾年土壤修復行業比較熱。2015年,咨詢項目接近1000個,金額約5億元,包括調查、風險評估、方案設計等;工程項目130個,簽約額達到21.28億元。從業單位和從業者數量加速增長,2015年年底分別達到930家和8000人。一些其他領域的“巨頭”也跨界進入土壤修復市場,通過投資并購等方式進入這個行業。土壤修復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然而,陳吉寧部長的一席話,似乎給這個火熱的行業潑了些冷水。他說,“土十條”治理土壤污染,是個“大治理”過程,不是要投入幾萬億元。我們強調的是風險管控,通過改變土地使用方式,而不是簡單依靠巨大的資金投入,對污染的土壤要加強監測監控,不讓污染繼續發展。
業內人士認為,強調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是基于土壤污染特點、治理規律所做的判斷。“不依靠巨大資金投入,而代之以改變土地使用方式、加強監測監控、不讓污染發展,看似是土壤修復行業的利空,其實是用更科學的方法管控和治理土壤污染,避免在底數不清、標準和技術不完善、商業模式不清晰的情況下盲目大量投資,長遠來看是行業的利好。”高勝達這樣理解。
風險控制的前提是對污染場地進行科學的健康風險評估。堯一駿表示,不同于國外,國內污染場地風險評估的對象往往為修復后場地上居住的居民,對于未來的影響,只能結合當前土壤監測數據借助數學模型進行預測,如何將風險評估做得科學合理,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研究與科技攻關。
對污染場地,很多人希望趕緊將其修復好,其實更科學的方法是“分類管理”。“沒有足夠的技術儲備和經濟能力,zui好少翻開那些已經嚴重污染的場地。不能修復賺了錢,還二次污染了環境!”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王金南呼吁。
面臨主要難題是什么?
修復效果參差不齊,根子在責任不清。修復圖快,易二次污染
2015年我國污染場地修復的投入為20多億元人民幣,約占GDP的0.03‰;而同時期美國的投入大約為180億美元,占GDP的1‰左右,意大利用于棕地(城市污染場地)再開發的投入占到其GDP的2.5‰。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土壤污染形勢更為嚴峻,投入相對不足。
上海市環境工程設計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益告訴記者,由于資金有限,目前國內污染土壤修復項目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地段較好的建設用地上。地方政府或開發商都愿意“埋單”,將一些工業污染場地修復后作為儲備土地,再進行商業開發或住宅建設。修復企業也會重點選擇參與一些財政補貼多、土地開發價值高的項目。
然而,即使是這些“千挑萬選”出來的項目,修復結果也并不盡如人意。高勝達表示,目前,在土地開發產生的修復需求中,業主和修復企業偏愛快速修復方式,易發生二次污染,環境隱患較大。
“之所以修復效果參差不齊,關鍵是土壤修復行業存在責任不清的根本問題。”高勝達表示。
2013年,國務院印發《近期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通知明確要求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督促企業落實土壤污染治理資金。但由于土壤污染具有漸進性和隱蔽性等特征,土地可能幾經流轉,一旦發生污染事故,原來的污染肇事方難覓蹤影,誰為污染場地修復埋單?
高勝達說,追究污染者或責任方的責任還沒有被充分重視,導致污染及其治理修復過程衍生許多問題,或是找不到明確的責任承擔者,或是由政府、環保部門、修復企業、咨詢單位等承擔。常州污染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只有污染者或責任方對污染及其導致的一系列問題負有zui終責任,他們才會積極主動地接受環保監管,做好污染責任管理,減少或者杜絕不合理低價招標和發包,對咨詢單位和修復企業高標準嚴要求,真正保護和治理好土壤環境,使土壤修復行業走上優勝劣汰的良性發展軌道。”
“修復資金總額有限,要讓其發揮zui大的效用,修復必須基于科學合理的健康風險評估,而不是基于當前場地的修復預算,有錢的可勁兒花,沒錢的草草了事。”堯一駿表示,各方正期待“土十條”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盡早出臺,以綱領性文件、嚴格的政策措施,開啟土壤污染防治的新紀元。
合作伙伴
|
相關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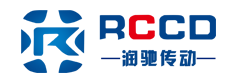













 關注微信
關注微信
 掃描手機二維碼
掃描手機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