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1日,國務院發布《控制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實施方案》(國辦發【2016】81號文,簡稱“實施方案”),進一步落實中央關于改革環境治理基礎制度的部署,對污染物的排放者和管理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國的環境治理基礎制度要進行系統性的大改革——這在中央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就已經有了綱領性的文件要求,基礎改革的內容包括“建立覆蓋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業排放許可制”、“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和“開展環保督察巡視”等等——這些重大變革都已在2016年拉開帷幕。
近日,我國多地大面積的霧霾正牽動著人們的神經,而被環保部“確診”為主要污染源的工業源依然難辭其咎,無論是在排放量上,還是在可控程度上都還是個“老大難”——超標普遍,造假不斷,新聞媒體上不斷刷新多路環保督查組“曝光式”的公告。固定源管理的難題亟待尋根問底地得到解決。
在2016年接近尾聲之際,醞釀多年的排污許可制度終于展現了藍圖。
“實施方案”中的關鍵詞
“實施方案”發布后,其中不少“關鍵詞”立即牽引了人們的視線,引發關注和熱議——“固定污染源環境管理的核心制度”;“整合”現有制度;“一證式”管理,“減輕企業負擔”;企業要建立“排污臺賬”和申領、核發、監管流程“全程公開”,等等。
“這些措辭完全是顛覆性的,真要成為現實,將重新定義現行的固定污染源管理制度,企業和管理者之間的關系也將發生重大的改變。”一位環境經濟學專家興奮地評價說,同在一個微信討論群的另外幾位學者當即對此表示贊同。
其實,早在一年前國合會的年會上,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就已經“預告”了許可制改革zui終目標:以排污許可制度為核心,整合各項環境管理制度,建立統一的環境管理平臺,實現排污企業在建設、生產、關閉等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全過程管理;實行一企一證;實行“一證式管理”;明晰各方責任,強化監管,落實企業的誠信責任和守法主體責任,推動企業從被動治理轉向主動防范……
這之后,排污許可制改革成為了環保部承擔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成為了整個環保界和企業界重點關注的話題。2016年1月11日,環保部成立了排污許可證實施領導小組,并設置了綜合組、大氣組和水組3個工作組,時任環保部總工程師的趙英民負責牽頭。從那時候起,領導小組就開始討論、起草、審議、修改包括“實施方案”草稿在內的所有的改革文件。在參考國際上已有的成熟理論并與三十年來的環保管理實踐經驗相結合的基礎上,領導小組又展開了密集的地方調研、行業調研,經歷數十輪的專題討論和多次的征求意見,以“實施方案”為“頂層設計”的排污許可制度改革正式全面啟動。
等待多年的路線圖
“我們一直缺的就是環保制度的頂層設計,”環保部原總工程師楊朝飛告訴《世界環境》:“從70年代起,中國的環保制度建設就起步了,可以說門類早就比較齊全了——從事前預防的,到事中、事后監管的,都有了。這些制度在不同層面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也在不同的階段解決了一些緊迫而突出的環境矛盾,可是zui大的問題,圍繞著污染源的不同環境管理制度之間銜接不上。”
楊朝飛解釋說,區別于很多發達國家對企業貫穿全生命周期的“過程式”的管理,我們的環境管理是“環節式”的,一個環節,一套人馬,手握一項行政權力,負責一個管理的階段,對企業的要求缺乏邏輯上的一貫性。
比如說,環評的就管環評,提了要求就給批了,也不管后面到底能不能落實,總量核查的不管達標排放,執法用不了在線監測數據,有時候會發生重疊——哪些企業、哪些污染物應該管、怎么管,各職能部門都各自有一套邏輯,不同的要求常會發生沖突;有時候又是脫節的,比如環評報告批復文件中對企業在某地的排放行為可能提出很多更嚴格的要求,但是按照現行的法律,只要企業在實際生產活動中的排放不超標,環保部門就算發現了企業沒有執行環評的要求,也沒有辦法落實處罰,導致環評“落空”。看起來干了很多工作,但是管理的實際效果并不好。
他告訴《世界環境》,排污許可證制度在國際上早已經是被廣泛采用的成熟的制度,是對固定污染源實行“過程管理”即全生命周期“一證式”監管的基礎性制度。這項制度的建設也是在第一任環保局長曲格平時代就提出來了,那個時候許可證是作為環保制度建設的“新五項”之一,也正因為它只是“之一”,而沒有明確其基礎性,統攝不了其他制度,所以也一直“難產”。不僅如此,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環保一直就沒有明確環境質量目標的核心地位,許可證制度實際上也并無大用場,也就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殘缺擺設。在楊朝飛當環保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期間,從07年到09年,國務院曾連續三年把排污許可制度的立法列入立法計劃。
“但思路都不清楚,怎么能列入計劃呢?過去長久以來,許可證跟其他制度的關系沒有理順,就一直連許可證條例都出不來臺。”楊朝飛說,這就是許可證制度雖然提了幾十年,卻一直未能建立起來的內在原因。
在江蘇省環保廳廳長陳蒙蒙看來,環境管理轉向以環境質量的改善為核心,實現現代化、精細化的環境管理,排污許可證制度的建立是必經之路。2016年的全國“兩會”上,陳蒙蒙告訴《世界環境》,江蘇過去雖然一直都有在發“排污許可證”,比如在蘇州工業園區,那些外企也都拿到了基層環保局發給他們的“排污許可證”,外企就理所當然地覺得,這就是法定給他的許可了。但是,驗收、三同時等等環保制度的要求都跟它不一致,從實際管理的意義上講發揮不了作用。地方也覺得很著急,一邊自己探索著改革的同時,也向環保部提出過建議和疑問,比如說排污權應該如何“確權”,跟環評制度應當如何銜接,等等,還在不斷的探索改革路線。然而,一些方向性的爭議終究需要國家層面來定調。
許可證到底是什么?
十年了,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宋國君眼里,這十年是他在孤獨中堅持研究許可證的十年,也是中國環保失落的十年。一直到2015年,環保部打響了“以環境質量為核心”的轉型攻堅戰,許可制改革開始醞釀,他才欣喜地看到轉機。2016年年初,環保部排污許可證實施領導小組請他作為專家組成員,一同參與了改革路線頂層設計的討論。
“過去十多年,國家搞總量減排,課題經費多,于是大家就更愿意圍繞著總量控制去做環境管理的研究,但是做許可證研究的話就沒什么項目可申請,只能自己想辦法找路徑去做。”宋國君說:“現在,終于要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了。”
他向《世界環境》解釋,成熟而完善的排污許可證并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理解的掛在墻上的一張證,它的“真身”通常都有幾十頁到上百頁不等,承載的是政府對一個向環境排放污染物的企事業單位的所有環保要求。
“所有”的環保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企業能被允許排放些什么類型的污染物,是直接排河里呢還是排進綜合污水廠呢;是通過高煙囪排出去呢還是大面積揮發性的排出去的呢;排放污染物的濃度和頻率限值是多少;一定時期內的排放量zui大能是多少;企業自己要做好哪些監測和記錄;要多久上報一次排污記錄;特殊情況下需要采取什么應急措施保障怎樣的排放限制,等等。
“比技術性的載明內容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回答許可證到底是什么,它扮演什么角色,目的是什么。”環保部排污許可證實施領導小組一位成員說:“這個問題以前一直沒有說清楚,但是中央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已經明確了方向。目前國家發布的‘實施方案’基本思路是與成熟的國際經驗接軌的,它是我們多年來環保管理經驗教訓的總結,也是按照我們目前的現實基礎制定的改革路線圖。”
他解釋說,根據“實施方案”,排污許可證是“企事業單位在生產運營期接受環境監管和環保部門實施監管應當遵守的主要法律文書。”這里面就包含了兩層含義:其一,它是用來約束企業的,企業要“按證排污,自證守法”,其中的重點就在于對排放行為的“許可”怎么定;其二,它也是用來約束政府的,環保部門要“依法發證,依證監管”,重點在于作為一項制度要如何保障執行。而“所有企業都要持證排污,按照所在地改善環境質量的要求承擔相應的污染治理責任”則是明確了許可證存在的目的是圍繞環境質量改善的中心工作服務,環境質量的改善是唯一目標;“制度統領”和“一證式”管理的定位則描述了許可證制度的基礎性地位,對固定污染源的諸項管理制度而言,它既不是附屬,也不是并列,而是一個基礎平臺,其他所有相關的制度、要求,都要經歷配套的改革銜接、融合進來。
過去的許可證管理之經驗與困惑
早在2010年,為了配合“十二五”的總量減排工作,浙江省制定了地方的排污許可證暫行辦法,嘗試著以許可證作為排污權的載體,落實總量減排任務并推動排污權交易。
浙江省一位基層環保官員告訴《世界環境》,客觀的說,浙江省的排污許可制度設計從一開始還是力圖吸收國際成熟經驗,希望藉此搭建現代化、精細化的管理平臺。從許可證的內容上看,不僅包含了污染物種類、濃度、數量、排放方式、排放位置等信息,也包含了產生污染物的主要工藝、設備以及污染物的處理方式和流程,試圖做到全過程管理;除此之外,浙江省的管理辦法還規定了排污單位應當建立污染物排放和污染治理臺賬,記錄排污許可證許可事項的執行情況,這是對排污臺賬制度的先試先行,2014年之后,浙江省還開發出了“刷卡排污”系統,從技術角度更加精細化、信息化。
不過,從執行的情況看,浙江省的許可證改革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效果。在2015年12月環保部組織召開的排污許可證制度國際研討會上,時任浙江省環保廳總量處副處長的陳俊表示,在過去的實踐中,浙江省的排污許可制度除了法律支撐不足、定位不清晰、管理范圍窄、證后監管弱等問題外,與其他污染源管理制度也存在相互獨立、分頭管理和管理效率低的問題,其作用并沒能很好的發揮出來。目前,浙江省再次展開制度改革,以排污許可證作為許可、核定、監管所有排污行為的基本管理制度,探索制定污染源“一證式”管理模式。
但在宋國君看來,浙江省的排污許可證難以發揮真正的作用并不僅僅是因為上述制度缺陷造成的實施障礙。更為關鍵的原因在于,浙江省的許可證設計思路就存在問題——它并不是為了控制企業的排放行為對環境質量的影響,而是附屬于總量減排制度的一項工具,是用來分解總量控制指標的載體,以行政區為單位分解的污染物排放總量指標是跟實際的環境質量目標脫節的,總量數字自身都是一筆“糊涂賬”,被“降格使用”的許可證自然就難以發揮其基礎制度的功能。
在對浙江省排污權交易市場的調研過程中,宋國君和他的研究團隊發現,企業獲得初始排污權的許可排放量普遍遠大于企業的實際排放量,而初始排污權是企業向政府買來的,計算依據是總量控制的任務和企業的績效水平。調研中,也有企業直言不諱地說,排污權交易系統的建立如果是以賣初始排污權來收費為目的,就起不到以經濟手段刺激減排的作用。“我的指標完全夠用,有什么動力再去實施技術改造進一步減排呢,大家的指標都用不完,誰還用得著去買別人的呢?”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總量控制的改革方向就已經確定為“實行企事業單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而不再是地方政府的總量控制制度。在國務院新發布的“實施方案”中,許可證和總量控制制度之間的關系得到澄清——要改變單純以行政區為單元層層分解總量指標的方式,通過實施排污許可制,落實“企事業單位總量控制”要求。總量考核要服從質量考核,在環境質量不達標的地區,要通過提高排放標準或加嚴許可排放量,對企事業單位實施更為嚴格的總量控制。也就是說,現在的總量核算的原則都要修改,許可排放量要“自下而上”地生成,與當地實際的環境質量要求掛鉤;而不是“自上而下”由國家下任務層層分解。“實施方案”同時還規定了,排污權交易的前提是“通過淘汰落后產能、清潔生產、污染治理、技術改造升級”之后,產生的“削減量”那部分,可以在市場上交易出售。也就是說,“有效削減量”才是排污權交易的基礎,這就從源頭上防止了指標倒賣、騰挪乃至于偏離減排目的的排污權交易,讓經濟手段更有效的發揮作用,讓守法者、少排污者受益。
合作伙伴
|
相關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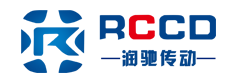













 關注微信
關注微信
 掃描手機二維碼
掃描手機二維碼
